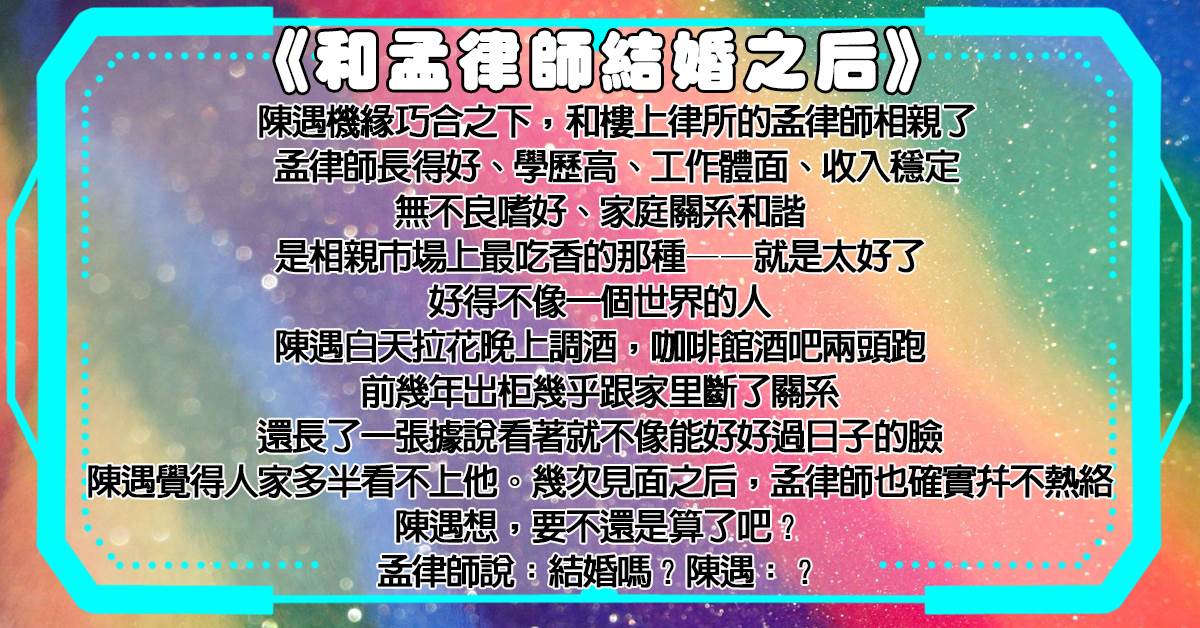《和孟律師結婚之后》第84章
陳遇聽他問才想起來要量體溫。
還是低燒,不過比早上高了半度,他甩了甩溫度計:“沒事。”
“多少度?”
“三十七度……”陳遇不想他擔心,準備往低了報,但是孟律師那樣看著他,哪怕是隔著屏幕陳遇也知道被他看穿了,慢吞吞地又吐出個九來。
“快三十八了。”孟律師表情有些肅然,眉心聚攏,“要不要去醫院看看?”
“不用,其實沒什麼不舒服。”陳遇想了想,寬他的心,“以前也這樣過,可能有點累,休息好就沒事了。”
“那你好好休息,洛秘書說,明天去的那家公司附近有家糖葫蘆店,你退燒了我給你買糖葫蘆。”
“不退不給我買嗎?”
孟廷川不說也就算了,陳遇的口腹之欲并不重,以前也不愛吃糖,他這樣一說,陳遇還挺想嘗嘗的,尤其是和孟律師一起嘗嘗。
“不退送你去醫院。”他一副嚇唬不聽話的小朋友的語氣。陳遇笑起來:“你跟蕓蕓也是這樣說話的嗎?”
孟律師說:“蕓蕓生病了自己會吃藥。”
陳遇說:“我也會吃藥。”
孟廷川也笑道:“藥給你買了,一會兒跟午餐一起送來,你記得用。”
“好。”
陳遇應得快,以為孟廷川說買了藥,應該是退燒藥或者消炎藥,沒想到還有外用的,他吃了消炎藥,糾結一會兒拿著藥膏去浴室了。
說起來有點好笑,他都三十多了,孟律師還給他畫這種乖乖養病,好了給你買糖吃的大餅,他還挺受用。
但是藥膏用了兩次,消炎藥吃了三頓,孟律師處理完工作,糖葫蘆都給他買回來了,陳遇還是在低燒。
陳遇自覺除了精神短、有點乏力之外一切都好,連腿都沒那麼酸了。
窗邊有一把休閑椅,他盤腿坐在上面,在太陽底下吃冰糖葫蘆。
孟律師帶回來的就是最普通的糖葫蘆,里面是山楂,外面是糖衣。
山楂都去了籽,個頭很大,也不那麼酸,糖衣薄薄的,在陽光底下晶瑩剔透,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脆微微帶著酸。
陳遇很多年沒有吃糖葫蘆了。但他確定他當年吃過的糖葫蘆絕對不是這個味道,山楂又小又酸還有籽,糖衣厚得快咬不動。
山楂個頭大,陳老板吃得文雅,幾口一個地吃,也不慢,沒一會兒一串五個的糖葫蘆就剩兩個了。
他舉著竹簽問:“廷川,你吃嗎?”
孟廷川在看手機,聞言抬頭看過來,看見陳遇嘴角沾了點糖沫:“吃。”
陳遇把竹簽橫過來,往他的方向遞了遞,糖葫蘆就在孟廷川嘴邊。但是孟律師抓著他的手腕,輕輕推開了糖葫蘆,湊過來卷起他唇邊的糖渣,旋即起身:“吃過了,甜的。”
陳遇知道他偏愛甜口,沒再喊他吃山楂,繼續小口啃。
孟律師又在擺弄手機了,陳遇問他:“還有工作嗎?”
“不是工作,在聊天。”孟律師連聊天對象都主動交代了,“林鶴書。”
陳遇覺得這個名字有點耳熟:“他是林老師的?”
“侄子。”孟廷川說,“他是大夫,找他問問。”
問什麼陳遇也知道,肯定是跟他有關。
他不去醫院是因為他清楚什麼原因。況且這樣的低燒,陳遇當年酒吧工作的時候也沒少有,常年熬夜,飲食作息都不健康,時不時就要小病一場,不嚴重的基本熬一熬也就過去了。
他站著調酒一晚上都未必有人能看出來他在發燒。
現在往返的機票錢能抵當年一個月工資,陳遇也只是早睡早起,多了一年一次的體檢,盡量不去醫院的習慣跟從前沒什麼變化。
他是覺得沒必要,還不至于諱疾忌醫,想到林教授的家學淵源有點好奇:“他也是中醫嗎?”
“是。”
“中醫還管這個啊?”陳遇沒怎看過中醫,也不了解,“我以為中醫就是吃中藥的。”
“中醫也有外科。”孟廷川笑了笑,“別的大夫我不清楚,他一定了解。”
陳遇覺得他話里有話:“他也是嗎?”
“嗯。”
陳遇對別人的故事并不好奇:“那他怎麼說的。”
“他說低燒可能是有炎癥,要我注意觀察。”
“觀察?”陳遇整個人都僵住了。
孟律師說話的時候特意加了主語,不是要陳遇注意,而是他觀察。他們雖然已經是不純潔的肉體關系了,陳遇還是想保留最后一點點距離感。
“我在吃消炎藥,你買的那個藥膏也用了,沒事的。”
“嗯。”
但晚上還是觀察了,孟律師用了點不那麼光彩的手段,他用親吻和溫柔撫摸包裝出了一個甜蜜地陷阱,陳遇毫無所覺,就那麼踏進去了。
然后就任人擺布了。
“有一點腫。”孟律師說。陳遇沒想到他這樣,雖然配合著沒有掙扎,聲音聽起來卻好像要哭了,他腦袋埋在枕頭里,聲音傳出來悶悶的:“廷川,不要看我。”
“乖,很快就好。”孟律師拿了藥,陳遇自己用藥多少有點草草了事,孟廷川要細致很多,里外都注意了。
等上完藥,陳遇是真的掉眼淚了,不是疼的,是羞的。他可以接受親密地接觸,但是在別的情境下,他沒有做好這樣毫無保留地準備,尤其是,單方面的。
孟廷川拿濕巾擦掉手上的藥,摟著他,親親他的眼睛,沒有說什麼安慰的話,而是問他:“阿遇,你設想過將來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行動不能自理的情況嗎?”
VIP專享
-
完結458 章
《逢春》馮橙 陸玄
馮橙眼前是一片黑暗,仿佛脫離了軀殼的靈魂飄在迷霧中,觸摸不到絲毫真實。 她心頭一點點升起疑惑:她隱約記得自己死了,現在是怎麼回事兒? “喵喵喵——”忽然,一聲接一聲的貓叫傳來,透著急促。 聽著這熟悉的貓叫聲,馮橙就越發疑惑了。 這貓叫,好像是—— …… 噠噠噠,馬蹄聲傳來,很快一名騎著馬的少年由遠而近。 少年一身黑色勁裝,愈發襯得膚白如玉,眸若寒星。 道上不見其他行人,只有路兩邊近人高的草木在這春日里肆意生長。 少年一勒韁繩,身下駿馬放緩了速度。 他翻身而下,環視一番往草木最繁盛的一處走去。 那匹被留在原處的大黑馬望著主人被草木掩映住的背影乖乖等著,顯得極有靈性。 草葉掃著少年墨色衣擺,露水悄然留在那雙皂靴上。 少年不準備往前走了,停下身形,手按上腰帶。 這時,他突然聽到了奇異聲響。再細聽,那聲音似是貓叫,又似是嬰啼。 少年眼中有了戒備,環顧四周。 入目皆是草木,仿佛無邊無際。 這樣的地方,無論是貓叫聲還是嬰啼聲,都很古怪。 忽然一陣微風拂過,草木搖擺,那若有若無的聲音真切了些。 少年決定去看個究竟。 草木很深,趟過去濕氣就染了衣,突然一物迎面撲來。 少年下意識側開身,一掌揮過。 慘烈的貓叫聲傳來。 少年定睛一看,就見一只棕黑紋相間的花貓摔在地上,那雙綠色的眼睛露著兇光,正警惕瞪著他。 原來是一只野貓。 少年解了惑,余光瞥到一處,突然定住。 不遠處橫躺著一個人,準確地說是一名女子。 少年沉吟片刻,不顧花貓的嘶叫走過去觀察。 那是一名十分美貌的少女,這般瞧著只有一些擦傷,可看她雙目緊閉悄無聲息的模樣,應當兇多吉少。 少年伸出手,去探少女鼻息。 肌膚冰涼,鼻息全無。 果然是死了。 看著那應該比他還小些的少女,少年不知怎的想嘆氣。 人既然已經死了,那他就沒必要留在這了。 這般想著,少年轉身往回走。 那只摔在地上的貓又叫了。 少年腳步一頓,看向那只貓。 花貓掙扎了一下,沒有站起來。 少年皺眉。 他剛剛出手重了些……罷了,那就順便把這只貓兒帶回城中吧,好歹是條性命。 少年向花貓走了兩步,忽地轉身向少女走去。 罷了,既然連貓兒都順便帶回城中,那順便把這橫尸荒野的少女挖個坑埋了吧。 真是晦氣,他明明只是趕路太久,想找個隱蔽的地方方便一下而已。 少年留意過有一片平地適合葬人,于是伸手搭上少女肩頭,準備把她抱起來。 那雙緊閉的眸子突然睜開了。古代|甜寵|HE|救贖|玄幻言情|權謀|大女主|言情69.3萬字 5 0 -
完結676 章
《當綠茶女配開始自暴自棄》 柳萋尋 季安
柳萋尋睜眼的時候季安的動作還在繼續,并且還越來越不克制。 她不舒服的動了動,目光落在總裁休息間的天花板上,想到剛剛暈過去時做的那個夢,她整個人還有些恍惚。 而季安感受到她的動作,眼底越發灼熱,動作也越發用力。 柳萋尋再次被他弄暈了,光怪陸離的畫面又出現了。 她所在的這個世界居然是一本叫做《總裁追愛小甜妻》的狗血文。 而她拿的則是反派劇本! 書中她宛如得了失心瘋,沒有任何智商可言的各種作死。 最后書里的男女主幸福在一起,她這個花式折騰女主,還得了喉癌的大反派被一刻鐘都忍不了的男主扔到非洲凄慘死去,而她的親弟弟妹妹還拍手叫好,各種跪舔男女主! 在徹底陷入黑暗前,她只有一個念頭:季安,你個王八犢子,老娘要和你一刀兩斷!現代|甜寵|HE|穿書|女配|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103.0萬字 5 0 -
完結2311 章
《穿越遠古野人老公霸道寵》葉清心
遠山,層巒疊嶂,森林中一片靜謐,空氣格外悶熱。 葉清心的汗水噼里啪啦的從額頭上掉下來,落在眼睛里,蟄得生疼。 然而此時,她卻不敢抬頭擦一下汗,保持著全身僵硬的姿勢已經幾分鐘了。 對面十幾米處,一頭體型像是小牛犢子般,雙眼閃著貪婪綠光的野獸,正在盯著她。 一張血盆大口垂著滴滴答答的涎液,長著黑灰色長毛的脊背微微向后拱起,隨時準備將一口她吞進肚里。 跑是不可能了,兩條腿的怎麼可能跑得過四條腿的! 打就更是做夢了,就她這九十多斤的小身板兒,估計還不夠這家伙一頓飯的。 “吼……” 野獸估計是等的不耐煩了,張開大口低吼了一聲,壯碩的身子向后一錯,便沖葉清心撲了過來。 完了完了,她真的要死在這鳥不拉屎的森林里了? 她從一個時空掉進了這里,還沒搞清楚自己穿越的是哪兒,就要變成野獸肚子里的粑粑了? 這也太慘了點吧,起碼讓她搞清楚這是哪兒啊……古代|沙雕|甜寵|穿越|腦洞|言情350.2萬字 5 0 -
完結596 章
《穿越成女神農》秦妙
深秋時節,天氣又干又冷。太陽像一個大大的蛋黃,隱在云層中,模模糊糊。 秦妙躲在村東頭的這堆柴垛上,凍得蜷成一團,身上的破棉襖不知道已經穿了多少年頭,灰黑的棉花一團一團的暴露在外。 之所以窩在這堆柴垛上不走,那是因為家里的土炕還不如這堆干柴垛暖和。與其面對家徒四壁的冰涼,還不如窩在這堆柴垛上曬太陽。 可太陽曬到了,麻煩卻也找上了門。 咚的一聲,一顆石子毫無防備的砸在秦妙的腦門上,被砸的地方頓時起了個大包。秦妙悲哀地嘆了口氣,說實話,她倒是情愿剛剛砸在腦門上的是塊大石頭,這樣被砸中之后弄不好就可以穿回去了。 許是見秦妙挨了一石子之后沒反應,接下來噼里啪啦的一大堆小石子扔了過來,然后一個賊眉鼠眼臉色黝黑的七八歲男孩兒跳了出來指著秦妙大笑:“傻子,傻子,大傻子!扔你石頭都不知道躲!哈哈哈!砸死你,砸死你!” 秦妙的心里很悲涼,倒不是因為被熊孩子欺負,而是因為非常不幸的穿越到這樣的一個破舊落后的農村而悲涼,吃粗糠,喝臟兮兮的河水就罷了,衣服里面長虱子啊!解手的茅房臟到看一眼一天都惡心的吃不下東西啊! 她認命的閉上眼睛,祈禱上那熊孩子的石子能扔的用力點,最好能把她砸死,也許一張開眼睛就能回到現代了。古代|女性成長|HE|金手指|穿越|大女主|爽文|現實情感|言情90.9萬字 5 2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