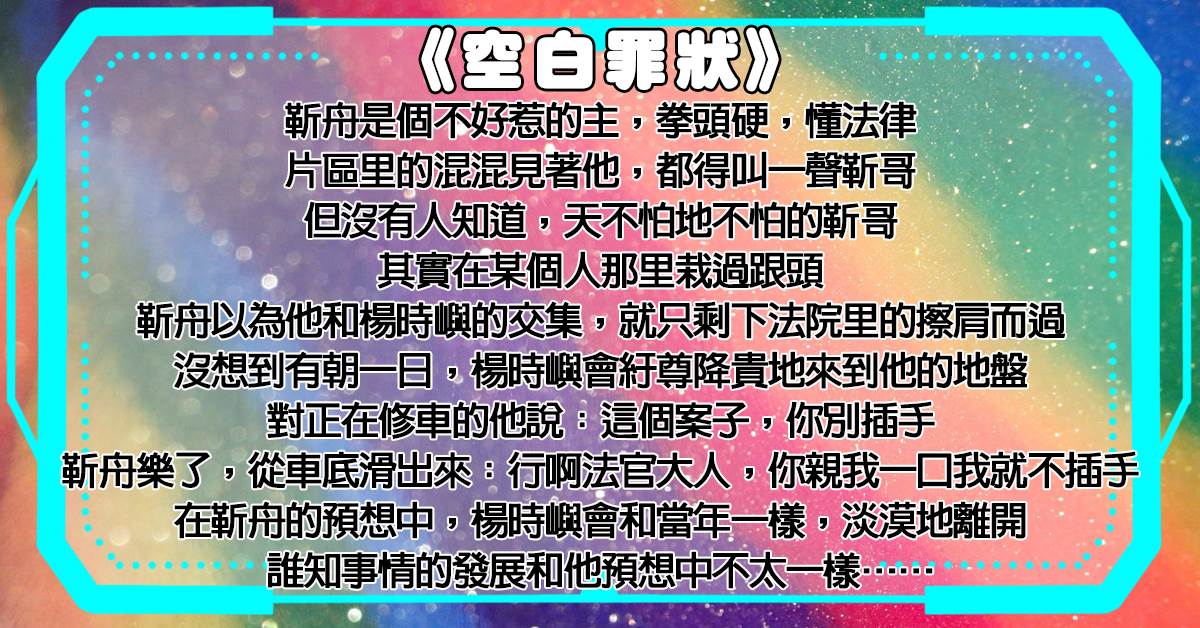《空白罪狀》第81章
“都好說。”靳舟選擇先穩住楊時嶼,“只要你還當法官。”
比起楊時嶼的職業前途,誰當老公誰當老婆這種事,都顯得不再那麼重要。
然而楊時嶼并沒有像以往那樣好說話,靜靜地看著靳舟道:“沒有‘都好說’這個選項。”
“你難道真的愿意放棄當法官?”靳舟著急地問,“至于做到這個地步嗎?”
“至于。”楊時嶼淡然地吐出兩個字,眼神里毫不摻雜開玩笑的意味。
完蛋。
靳舟的腦子里冒出這兩個字。
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很顯然楊時嶼現在就有光腳的打算,而靳舟反倒成了怕脫鞋的那一個。
“行行行,我讓你。”見楊時嶼完全不退讓,靳舟最終只有妥協,“你當老公,你是老大。”
“好。”楊時嶼重新牽住靳舟的手,臉上的表情仍然是云淡風輕,壓根沒有賭贏的喜悅。
靳舟立馬意識到,楊時嶼并沒有在跟他賭。
他是真的無所謂當不當法官,無論靳舟做出什麼選擇,他都會是這副不在意的模樣。
靳舟不禁有點害怕,握緊了楊時嶼的手,說道:“我們可說好了啊,無論如何,你都不準辭職。”
楊時嶼淡淡應道:“嗯。”
靳舟想到楊時嶼總是背著他單獨行動,又不放心地說:“你要是不當法官,你老婆就沒了你知道嗎?”
楊時嶼聞言輕聲笑了笑:“那你叫聲老公聽聽。”
兩人重逢以來,楊時嶼的臉上很少展現過笑容。而現在他就像是掌握了讓靳舟聽話的秘訣似的,那麼舒心,那麼放松地笑著,就連冰冷的防滑鏈在月光的照耀下都顯得柔和起來。
“咳咳,”靳舟不自在地別開臉,看著另一邊,“你倒是讓我適應適應。
”
靳舟口中說的適應,其實只是適應這個稱呼。
男人本就應該寵老婆,既然老婆想被叫作老公,那他叫便是。
只是一個稱呼而已,怎麼可能撼動他在床上的地位?
沒幾天后,侵占案終于開庭。
靳舟和劉茜約在法院大廳見面,劉茜就像是做賊似的,戴著一副夸張的蛤蟆鏡,見著身穿西裝的靳舟,把鏡框滑到鼻尖,打量著靳舟道:“舟子,你今天怎麼人模人樣的?”
靳舟無語地抽了抽嘴角:“姐,你還想不想要回你的表?”
“嗨,我就是說你今天可真帥。”劉茜走到靳舟身旁,“我有幾個好姐妹,要不介紹給你認識認識?”
劉茜不怎麼參加劉永昌這邊的聚會,還不知道靳舟是gay。
“別了吧。”靳舟戰術性后仰,“我可不想享受富婆鋼絲球。”
劉茜一巴掌拍到靳舟的肩膀上:“凈瞎說!”
今天來法院出庭,張瑞也帶上了他的律師,對方看上去年紀不大,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
此時法官還沒有入庭,興許是對方律師的氣勢讓劉茜感覺不妙,她拍了拍身旁靳舟的胳膊,小聲問道:“舟子,這表真的能要回來嗎?”
還未等靳舟回答,坐在對面被告席上的張瑞便主動接話道:“劉姐,我就沒拿你的表,你怎麼要回去?”
旁聽席上沒有別人,整個法庭里鴉雀無聲,也難怪劉茜小聲說一句,能被對面的張瑞聽到。
“你少給我裝孫子。”劉茜不愧是劉永昌的女人,哪怕此時心里沒底,嘴上也絕不饒人,“表要不是你拿的,老娘頭摘下來給你當球踢。”
是時法庭前門被人推開,主審法官走了進來,靳舟趕緊用眼神示意劉茜,不要再說多余的話。
案件的事實經過并不復雜,陳法官甚至都懶得看卷宗,就那麼聽著靳舟和對方律師的發言。
“所以現在那塊表還是不知所蹤,對吧?”聽完雙方訴求,陳法官將雙手環抱在胸前,手肘搭在桌子上問道。
“對。”對方律師說道,“原告污蔑是我當事人拿走了手表,但手表根本就不在我當事人手里。”
“行吧。”陳法官點了點頭,“下面進入舉證質證階段。”
靳舟先拿出了巴黎圣殿的監控視頻,毫不意外地,被對方律師反駁,說這樣的間接證據不能證明張瑞拿走了手表。
接下來靳舟又拿出了另一段監控視頻,也是來自巴黎圣殿,但時間稍晚,是張瑞在跟另一人喝酒時,手上明顯戴著一塊亮晶晶的手表。
“這是我當事人自己的手表。”對方律師繼續反駁,并從手邊拿起了一塊普通的男士手表,“就是這塊。”
由于證據清單在開庭之前就已提交,因此靳舟一點也不意外,對方會針對他拿出的證據提前做好準備。
而監控畫面太過模糊,根本看不清手表的樣式,也只能是對方說什麼就是什麼,靳舟沒法再進行反駁。
場上的形勢明顯對劉茜不利,她焦躁地摳著手指,看靳舟的眼神也越來越擔心。
“我方申請證人出庭。”對方律師始終維持著不緊不慢的語速,可見他對贏下這場官司是勢在必得。
張瑞已經松散地靠在椅子上,顯然是把自己抽離出來,像看戲一般欣賞著己方律師的表現。
其實靳舟也想過尋找證人,但他讓小武和虎子盡量找過,并沒有找到能派上用場的人。
VIP專享
-
完結67 章
《報告!方秘書成富婆了》方喬 杜聿
“我得和她分!就這麼著了!分!鐵定得分!”沈見微握拳在桌面重重敲下,像是在給自己鼓勁兒,“再不分我遲早要完。” 站在窗邊的人掛了電話,重新坐回桌邊,眼角微挑的眸子睨了沈見微一眼,不做聲。 “聿哥!您是我親哥!您是我爸!”沈見微朝他轉頭,眼里是輕易可見的惶恐,“你快幫幫忙吧!我要怎麼才能甩了她。” 杜聿還是不理會他,只自顧自喝酒。 沈見微的手機響起。 他煩躁地抓起來看了看,嗷一聲摔了手機,又干嚎起來:“她說她到樓下了!聿哥!她馬上要上來了!我要怎麼跟她說啊!” 杜聿被他吵得實在煩了,放下杯子,低低說了句讓她上來。男二上位|現代|HE|豪門霸總|大女主|言情10.1萬字 5 65 -
完結61 章
《半朵木槿花》夏依依 連家良
烈火在燒,天空赤紅一片。 狂風助長了火勢,自上而下,不可阻擋,頃刻間吞沒了整座山村。 山腳下,那個人光著腳,手上擰著一個塑料袋,瘦削的身影緊繃著,直到最后一聲哀嚎消失后才略略抖動了幾下。 “呸!“他朝山村的方向吐了一口痰,轉身離開。 那個小女孩漂浮在江面上,身上的粉色衣裙在水中如同散開的花朵。她雙眼緊閉,白嫩的脖子上有兩道淤青,已經死去多日。 警笛聲,哭泣聲,驚叫聲交織成一片,連日來的搜索在此刻終于畫上句號,但有些人,卻開始了和噩夢糾纏的一生。 女子站在樓頂,無神的雙眼注視著冬日的黎明。 ”沒有月亮,沒有星星,這算什麼夜晚?“ 她吐槽著,骨瘦如柴的手輕攏了下耳邊的亂發,然后縱身一躍,消失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現代|女性成長|HE|豪門霸總|復仇|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9.2萬字 5 41 -
完結29 章
《渣男就是甘蔗,越嚼越渣!》江稚魚 宋之堯
三周年紀念日,江稚魚收到的唯一“禮物”,是一條分手短信。 后來她才知道,原來那天宋之堯和前女友復合了。現代|女性成長|HE|娛樂圈|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4.4萬字 5 152 -
完結31 章
《在最愛他那年選擇放他自由》蘇清妤 溫照陽
電視機里,當WNG拳王爭霸賽官宣冠軍得主——- “恭喜本屆金腰帶得主,我們的新晉拳王——溫照陽!” 蘇清妤鄭重地將日歷上圈住的紅色桃心圈住。 為了這次比賽,男朋友溫照陽整整六個月零二十天沒有碰過她。 他說:“正式比賽之前,我都不能碰你,這是比賽規定。” 想到這里,蘇清妤拿起手邊的護士制服,心臟砰砰跳了起來。 他終于能“解禁”了。 而自己也終于盼來了這一天,他說過只要奪冠就將結婚提上日程。 長跑了七年,終于等到了這天。 …… 溫照陽進門時,蘇清妤腕上的心率檢測表已經超過70。 她走上前,心跳怦然:“照陽,恭喜你奪冠,今天我們……” 然而,她的話還沒說完。 溫照陽便忽然打斷:“我先去洗澡。” 沒有多余的話,沒有想象中的求婚,甚至連跟她分享勝利的喜悅都沒有。 他是太累了嗎? 蘇清妤拿過他扔在沙發上的外套掛起,沒多想。 這時,口袋里的卡片掉落在地—— “阿陽哥,戀愛一百天紀念日快樂!” 蘇清妤好似被雷擊,腦海里驀然浮現出一張明艷的娃娃臉。 顧青青。 溫照陽拳擊俱樂部唯一的女隊員。 只有她會叫溫照陽阿陽哥。男二上位|現代|先虐後甜|女性成長|HE|出軌|現實情感|言情4.7萬字 5 166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