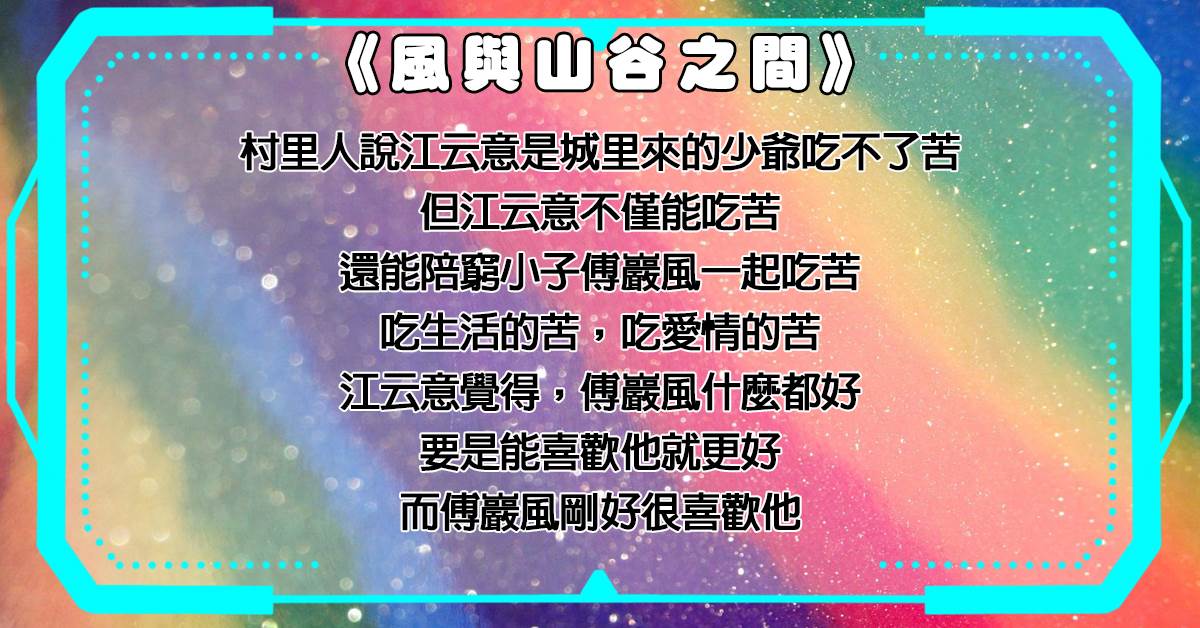《風與山谷之間》第29章
“你回來啦。”江云意撐著桌沿站起來。
一段時間沒見,江云意整個人又挺拔不少,腦袋上難得地不再是亂翹的呆毛,一頭短發修剪得利落漂亮。
一旁的吳文霞也跟著站起來,過來拉傅巖風的胳膊把他往桌旁帶,“你來看看小云送我們的干貨,咱家以前沒吃過的,這也不知道怎麼煮,煮壞了就不好了。”
沒吃過豬ro也見過豬跑,傅巖風光從禮盒的包裝也能知道一定不便宜,便問江云意花了多少錢。
“不到五十,就盒子好看,裝的不過是普通的干貨。”江云意回答他,轉頭對吳文霞說,“阿姨,你把它們當香菇煮就好啦,這些跟香菇干貝差不多的。”
吳文霞說:“香菇啊,那阿姨懂了,不過家里干貨好多了,下次人來就好了,不要破費,你來阿姨就很開心了。”
拿著海參和干鮑去灶間的吳文霞還在嘀咕:“香菇怎麼用那麼高檔的盒子裝。”
晚上吳文霞和傅巖風一起用那些干貨搗鼓出一鍋湯,一盒的海參鮑魚放了半盒下去,吳文霞喝一碗飽了,剩的傅巖風和江云意各喝兩碗。
“這個好吃。”吳文霞夾起一塊海參說,“滑滑的,跟香菇一樣。”
又夾起一塊鮑魚,“這個就硬一點兒,不過也好吃,有嚼勁。”
話題轉移到江云意身上,“小云最近好像是有長高一些吧?阿姨看著你是長高了。”
“高了高了!”江云意放下碗筷,要跟傅巖風比身高。
傅巖風低頭扒飯不配合他,江云意瞬間蔫了,吳文霞一副要親自把傅巖風從椅子上拉起來的架勢,于是傅巖風只好站起來了。
雖然江云意確實是比過年那會兒要高了,但跟傅巖風一比還是自取其辱。
吃過飯,吳文霞早早休息,兩人在后院一起洗碗。
傅巖風問他高考成績,一開始江云意抿唇不說話,傅巖風又問了一遍,這時候才聽見江云意說,“成績不好,沒有好大學可以上,可能要復讀,也可能不讀了……”
江云意語氣平靜,好像只是在說別人的事。
“不讀了?”傅巖風低頭洗碗,用隨口一問的口氣道,“出來打工?準備去哪個廠?還是拜哪個師傅當學徒?”
江云意低頭喃喃:“我遺傳我爸,不會讀書。”
傅巖風停下手上的動作,抬頭看他:“是不會,還是不想?”
“我不知道。”江云意突然帶了哭腔,“我不知道,干點什麼都好,我就想早點離開學校,早點離開家。”
“長大不是離開學校或者離開家,”傅巖風盯著他道,“而是有能力走到社會上去。”
江云意怔怔看著傅巖風,半晌抬起胳膊擋住眼睛,止住了眼淚。
兩人繼續洗碗,誰也沒再說話,約摸五分鐘后,快洗完碗的時候,江云意再度開口,跟傅巖風說了件事。
六月份剛高考完,親媽江惠清回來找他了,跟著傅平坤一起來學校。
江云意說:“她老了不少,跟照片完全不一樣了,我一開始沒認出來,是我爸說了我才知道她是我媽。”
又說原來江惠清不是跟男人跑了,是跟傅平坤離婚后自己一個人去上海打拼,現在已經買了房買了車。
“雖然我以前也怪過她丟下我,但好奇怪,我就是不討厭她。”
江云意沒說的是,其實剛見到江惠清的時候,他是極別扭不自在的,哪怕他一直以來都在用她的姓。
江惠清的臉他只在幾張舊照片里見過,所以在他印象中,親媽一直是二十出頭的模樣,而十幾年后的現在,江惠清已經老了不少,臉上爬了不少皺紋,笑起來比哭還難看。
那天傅平坤來學校,腋下夾著個公文包,手邊電話沒停過,抽空才跟他說兩句話,說他現在長大了,要跟誰走是他的自由。
江惠清過來拉他的手,沒能扯出一個像樣的笑,眼淚就先掉了下來。
江惠清對他說:“媽來遲了,媽現在有錢了,能養你了。”
他就像一個皮球,前十八年被踢到傅平坤那兒,十八歲以后又滾回江惠清身邊。
一路上江惠清都在問他這些年傅平坤對他好不好,劉賢珍對他好不好,他昧著良心說了假話,江惠清滿懷的負罪感好像才減輕了些,說著自我安慰的話:“你是男娃,媽就知道他們至少不會對你太差。”
江云意有好多話想說,但生活太復雜了,最后能說出來的只有小小的切片。
他從前看傅巖風再累都只是扛著,從不向誰埋怨生活的苦,現在他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不說,而是沒辦法說,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討厭傅平坤,所以一直自作主張用著江惠清的姓,等江惠清真的來找他時,他才發現自己并沒有想象中那樣高興,因為他沒辦法對江惠清缺席的這十幾年的時間視而不見,盡管江惠清告訴他,當年她是怕他跟著自己過苦日子才把他留給傅平坤。
江云意說:“跟我媽去上海待了半個月,成績出了,我媽讓我在上海那邊復讀,以后考上海的學校,我沒考慮好要不要復讀,跟我媽說暑假想回來待一段時間,就先回來了。
VIP專享
-
完結110 章
淪陷溫柔:我竟是港圈大佬白月光
向日葵永遠向著太陽,我永遠向著你。 ——寧熙VS盛宴 …… …… 南非。 開普頓,城郊。 燈光破開夜色,越野車碾成坑洼路面,停在廢棄廠房門前。 車門推開。 穿著黑色馬丁靴的腳,重重踏在積著雨水的地面上。 水花四濺。 幾道強光手電同時照過來,映亮來人的身影。 白T,黑褲,亞光機車外套。 長發利落地束成馬尾,一張精致的東方面孔展露無疑。 看年紀,也就是二十歲出頭。 臺階上,綁匪頭目微怔。 盛家竟然安排一個漂亮妞兒來送贖金? 寧熙抬起提著電腦包的右手。 “按照你們的要求,這里面存著一億加密貨幣。孩子在哪兒?” 綁匪頭目抬抬下巴,一個黑人綁匪邁步走過來,想要接過電腦。 寧熙抬手避開對方的手掌。 “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黑人綁匪抬起右手,AK47槍口頂住寧熙的太陽穴。 “東西交出來!” “保險箱有密碼,除了我沒人能打開。” 看也沒看那位黑人綁匪,寧熙抬眸對上綁匪頭目的眼睛。 “你們想要錢,還是想要我的命?” 綁匪頭目上下打量她一眼。 “外套脫掉,我要確定你沒有帶武器。” 寧熙脫下皮衣外套,隨手扔在一邊,抬著兩手緩緩轉了一圈。 目光掃過女孩子的纖腰長腿,確定她身上沒有武器,綁匪頭目轉身走進廠房大門。 “跟我來。” 寧熙跟上臺階,走進廠房。 除了門口的四人,廠房內還有七個人,全部都有武器。 沒有人蒙面,根本不在意被她看到臉。 寧熙瞇眸。 很明顯,這些混蛋根本就沒想,讓她和孩子活著回去。 廠房一角的紙箱上,坐著一個小男孩。 四五歲的年紀,小手小腳都被膠帶綁著,嘴里塞著一只手帕。 毛茸茸的羊毛卷下,一對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看著寧熙。 寧熙見過孩子照片,知道這就是被綁架的人質—— 港城盛家的小外孫盛世。 寧熙快步走過去,幫小家伙扯出手帕,解開手腳上纏著的膠帶。 “別怕,我馬上帶你回家。” 小家伙眨眨大眼睛。 “你是誰呀?” 沒哭沒鬧,還有心情問她是誰。 小屁孩,膽兒還挺大。 擔心被綁匪識破身份,寧熙摸摸小家伙的臉,向他眨眨眼睛。 “我是你舅舅的朋友,小時候我還抱過你呢,忘了?” 小家伙仔細打量她兩眼,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怪不得,漂亮姐姐這麼眼熟,舅舅電腦里的照片不就是她嗎? “舅媽,我終于見到你啦!” 寧熙:…… 小家伙不會是把“朋友”聽成“女朋友”了吧?都市|現代|熱血|甜寵|豪門霸總|大女主16.6萬字 5 385 -
完結21 章
我瞞著總裁老公偷偷懷了孕
我瞞著總裁老公偷偷懷了孕, 開始他沒當回事,只覺得我是突然變乖了, 他整夜的陪著初戀我也不吃醋了, 于是 他開口要初戀的孩子跟他姓,還要我和他一起養, 我笑著答應,只是手不自覺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上, 男人擰了擰眉:“收起你的小心思,我說過,不會和你生孩子。” 我故作憂愁:“可媽說,想讓我們生個孩子......” “那你就自己生。” 聽著他冰冷的話,我挑了挑眉。 他那麼大度,愿意照顧別人的老婆孩子, 那等我自己生了,他應該也愿意養,也能接受孩子的父親不是他吧, 我拿起手機,看著日歷。 10月31日。 兩個月后,我才可以做四維彩超, 到時候我會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懷孕了。 然后出國繼續修產科,生下不屬于他的孩子。 在這期間,我除了每天看著初戀和江霆夜撒嬌,日子和以前也發生了改變。 首先,我不再每月15號,隨著江霆夜去照鳴寺禮佛。 其次,我不再每江五,去老宅討好公婆。 而江霆夜也一直住在離初戀最近的客房。 時間很快過去,在離開的最后兩天 江霆夜終于發現衣帽間里,我一件衣服也沒有了。 “你的衣服呢?” 我平靜回:“都丟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以后我再買新的。” 我說的是衣服,可江霆夜卻隱約感覺出我話里的另一層意思。 但他沒多想,出聲嘲諷。 “江家的錢,你用的倒是順手。” 我沒在意,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再次醒來,我是被手機短信聲吵醒,打開一看,是京市航空發來的。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京市紐約 UT031 航班,將于今日14時 20分飛往紐約.……祝您旅途愉快。” 關閉手機,我又檢查了一遍行李, 不多不少,兩個行李箱。 是我在半山別墅五年的最后生活痕跡。 我打車直奔京市最大的娛樂傳媒公司。 “你好,我想請你們幫我寫個新聞,告訴我老公,還有我的公婆以及全世界一個好消息。” “我懷孕了,已經五個月了。” 負責人第一次遇到這種新聞,滿臉不解。 “這位女士,這種事沒必要寫個新聞吧?” 我拿出了結婚證,遞給負責人。 “我是江霆夜的夫人!” 我別人不知道,可江霆夜,誰人不知? 負責人瞬間愣住,一臉恭敬:“好的,我們馬上給您安排。” 我又從包包里面拿出了一張紙,遞到他面前。 “這是我們寶寶四維彩超單,麻煩你幫我上個熱搜,我老公會很感謝你們的。” 進機場前,我拿出手機給江霆夜發去一條微信。 “老公,今天下午三點記得看新聞報道,我給你準備了一個驚喜,希望你和你媽媽能喜歡。” 發完消息后,我摘下婚戒。 注銷了一切聯系方式,拔出手機卡,將戒指和手機一并扔進垃圾桶。 隨后,我頭也不回的走進機場。 坐在飛往紐約的航班上。 我看著窗外的藍天白云,這一刻仿若新生。 飛機劃破天際,永遠消失在了京市的上空。現代|女性成長|HE|豪門霸總|追妻火葬場|大女主|爽文3.2萬字 5 1634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1659 -
完結330 章
他的癮
【美強慘.腹黑偏執私生子x富家乖乖女】 直到未婚夫梁牧之在訂婚當天同人私奔,被拋下的許梔才幡然醒悟,真心未必能換得真心。 她看向那個一直默默在她身后的男人。 梁錦墨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了黑暗,但許梔給了他一束光。 “我這個人有些老派,從訂婚到結婚,到死,不換人。” 他問她,“這是一輩子的事,你想清楚了嗎?” 后來坊間傳聞,梁家兩位少爺為爭奪一個女人大打出手,意外的是私生子梁錦墨成為贏家。 世人都說他冷漠寡情,不近女色,許梔深以為然。 直至春夜月下,男人骨節分明的大手控著她纖細腰肢,菲薄的唇輕觸她白皙脖頸,火熱的指尖寸寸逡巡,攪亂了一池春水。男二上位|現代|治愈|暗戀|甜寵|HE|豪門霸總|青梅竹馬|言情50.1萬字 5 915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